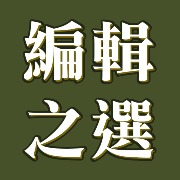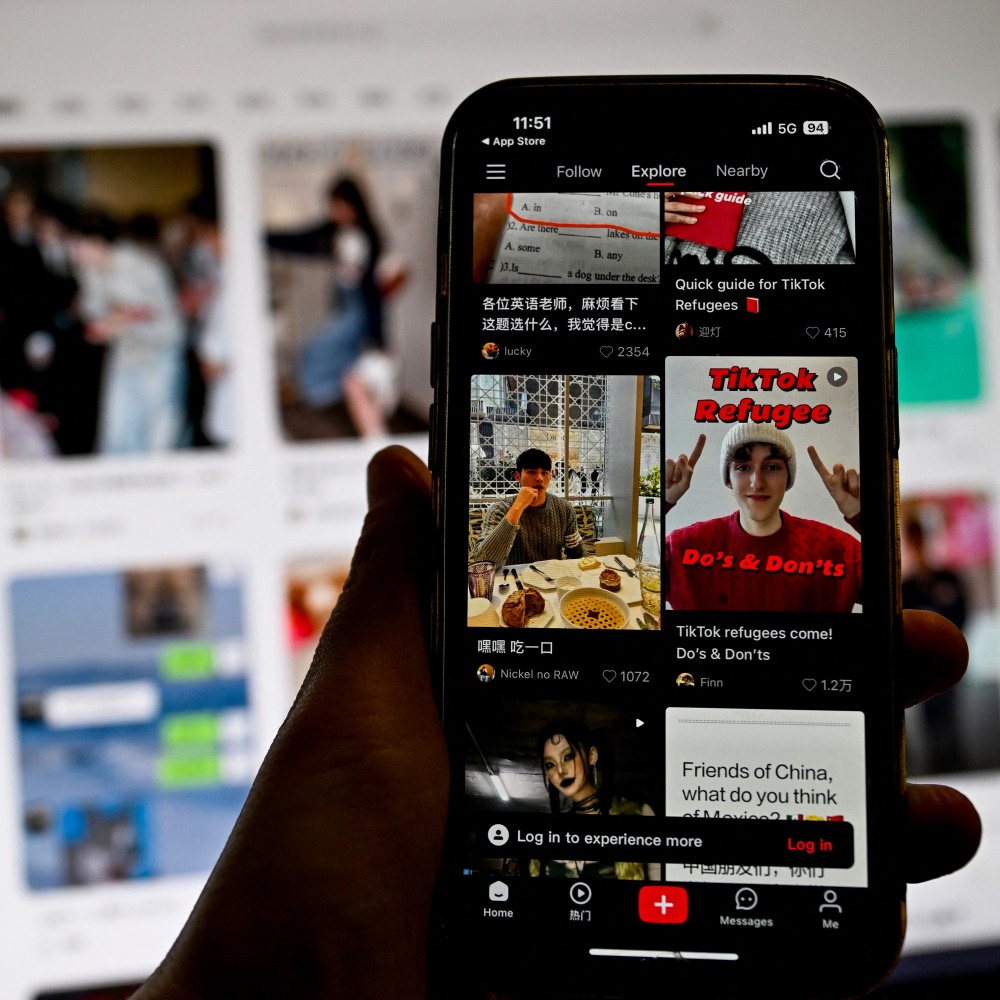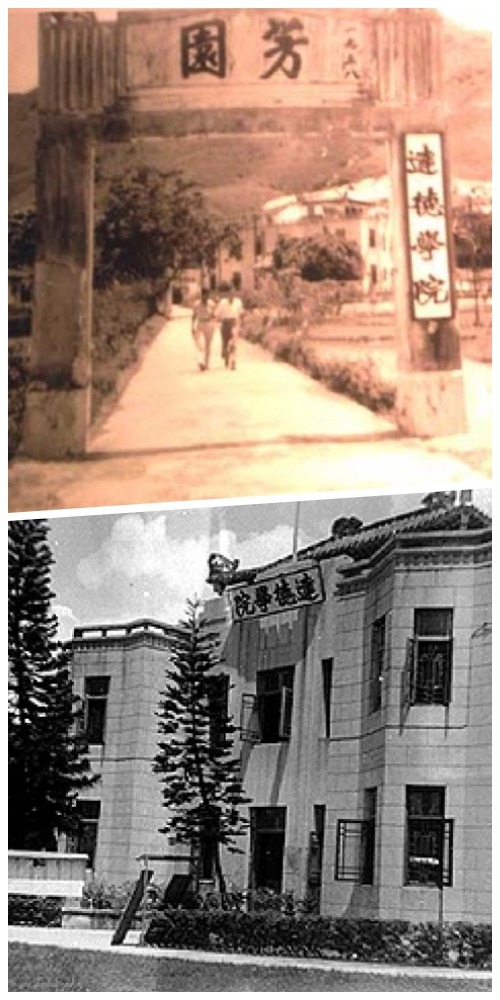刊登日期 : 2024-05-18
最近纪录片《何以中国》热播,让人们再次感受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魅力和生命力,同时也让大家感受到中国政治文明连绵不断的生命力所在。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范勇鹏教授在19/2/2024东方卫视《这就是中国》节目中就中国政治文明论述。
“中国”概念如何诞生?
中国概念的产生,反映了中华文明的一个基本特征,就是我们在应对共同威胁、维护共同生存的过程中,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向心力和对凝聚性的中央核心的认同。
我们今天为什么特别需要这样一个“中”字?
我们看上古时期,当时中国的地理规模已经非常大了,放在今天世界上就已经是一个大国;它的地理、人口和文化的多样性,也远远大于今天任何一个号称文化多元主义的国家。
我们经常会聊起欧洲为什么难以统一,很多人会说,是因为欧洲的地理破碎。
但是中国的地理也很破裂,比如蜀道难于登天的四川盆地、四塞之地的关中平原、表里山河的三晋大地、泰山屏障的山东半岛,似乎都不比欧洲的区域分隔更容易打破。我年轻的时候曾在欧洲游历,我觉得欧洲的地理空间其实比中国的要更容易翻越。

还有人说是因为文化的多元。
但中国是一个万国之和,统一到现在两三千年了,今天各地方言差异还不亚于欧洲各个主要语言之间差异。一位阿拉伯学者问:“中国人讲那么多不同语言都可以统一,我们阿拉伯人说一样的语言,为什么四分五裂?”
所以我们的条件并不是天生就容易统一的。中国人能够不断地走向更高的统一,它的根本,在于中国人所创造的文明、文化和制度。它的核心就体现在这个“中”字上。
以高超能力整合巨大国土
早自尧舜禹的时代,中国人就以高超的能力整合这块巨大的国土。
我们今天黄金周旅游,坐着高铁或者自驾车跑个上千公里就觉得自己很牛了,但是读《尚书·禹贡》,那个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把天下九州规划经营得井井有条。

有人说《禹贡》可能形成于战国,也有理想化的成分,但是我们今天考古工作所发掘出来的上古文明的规模,足够让现代人惊叹。
如果说夏商还有一定的军事强权和神权政治的色彩,那么到西周就进入一个新的阶段,我们完全靠一套政治和礼法制度把天下有效地整合起来。
如此巨大的一个国家,它最大的挑战是什么?是内乱。
法国的孟德斯鸠讲过一句话——“小国亡于外敌,大国亡于内乱”,而他讲的还是那种几万人到几十万人规模的国家。对于中国这种超大型国家,“建中立极”是消除混乱的法宝,也是我们从多少年战乱的惨痛教训中凝聚出来的智慧。
近代有一位大学者王国维(《人间词话》作者),也是一位非常好的历史学家。他在研究甲骨文的基础上分析了西周的制度,他认为其中一个关键点,西周要建立这套制度就是为了消除乱源。
他把政治制度分成两个层面:在中央层面,周公这些人是要建立稳定的权威,天子之位是不能随便都来争的,这个产权是要明晰的;而在运行层面,则要有充分的竞争,要选贤任能,不能搞世袭。
王国维把政治权威和治国理政这两件事情的逻辑讲得清清楚楚。其实今天人类政治依然面临这两个层面的问题,今天多数国家依然面临这样的问题。
秦汉以降,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取代了西周式的天子制度,郡县官僚制度取代了西周的封建制度,但是王国维讲的这两条逻辑——一个权威、一个治理——依然延续了下来,比如皇帝之位是不能随便争的,官员选拔也是要靠竞争的,最后我们发展出了科举。
秦制对现代国家制度的贡献往往被低估了,它的意义丝毫不亚于四大发明。
延伸阅读:“中国何以为中国”?从政治文明的角度解读

中央权威保障大跨度整合
无论周制还是秦制,它有了一个中央权威,就可以实现大范围的共同的安全秩序,提供广土众民生生不息的条件,产生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和市场空间,进行大跨度的资源调配和整合。
每逢乱世,中国人对这种中央权威的渴望,尤其深刻。
最典型的就是春秋战国那五百多年,所以诸子百家他们的观点各异,互相攻击,但是在政治理想上却有很大的一个共识。
比如:管子说“使天下两天子,天下不可理也”;孔子说“天下有道,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;孟子说“定于一”;荀子说“隆一而治,二而乱。自古及今,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”;韩非子说“事在四方,要在中央;圣人执要,四方来效”;《吕氏春秋》说“一则治,两则乱”。
这些都是历史中凝成的经验智慧。

因而,在中国历史中,我们看到地理、制度和文化这些因素叠加,构成了一个生命力顽强的中央结构,围绕它就形成了一个中国哲学家赵汀阳教授所讲的“旋涡模式”——不管是什么人,你参与到中国的历史进程中,最后都会成为中国人;不管是什么宗教、思想,进入中国都会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。
今天的中国之所以为中国,这个逻辑决定了。
在内部,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,要有一种向心性的制度和文化,让全国各族人民在团结凝聚中成就一个多元的利益和价值;在世界上,中国也要成为一种良性秩序的源头,向外辐射和平、合作、发展和公正,以及中国将带给世界的原则。(二之二)
(转载自《这就是中国》节目,标题及内容经编辑整理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