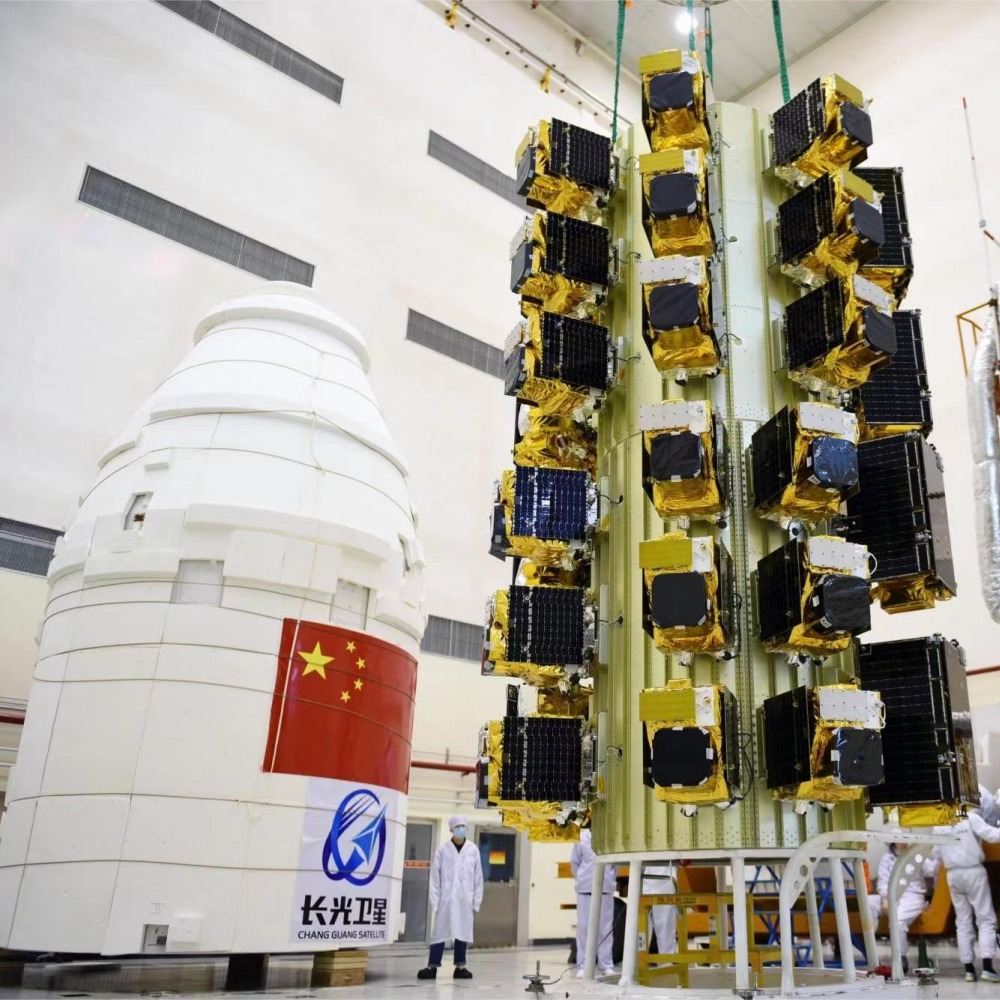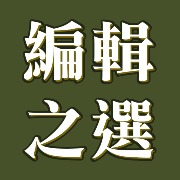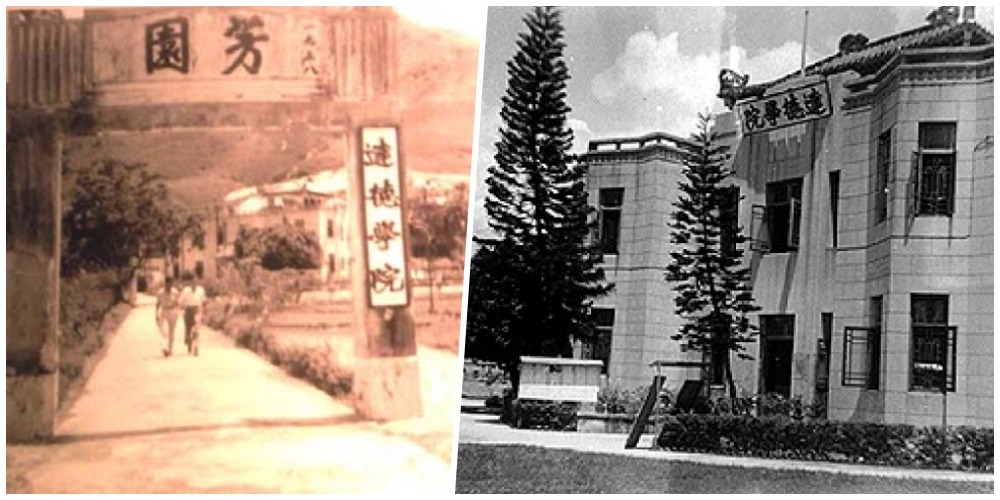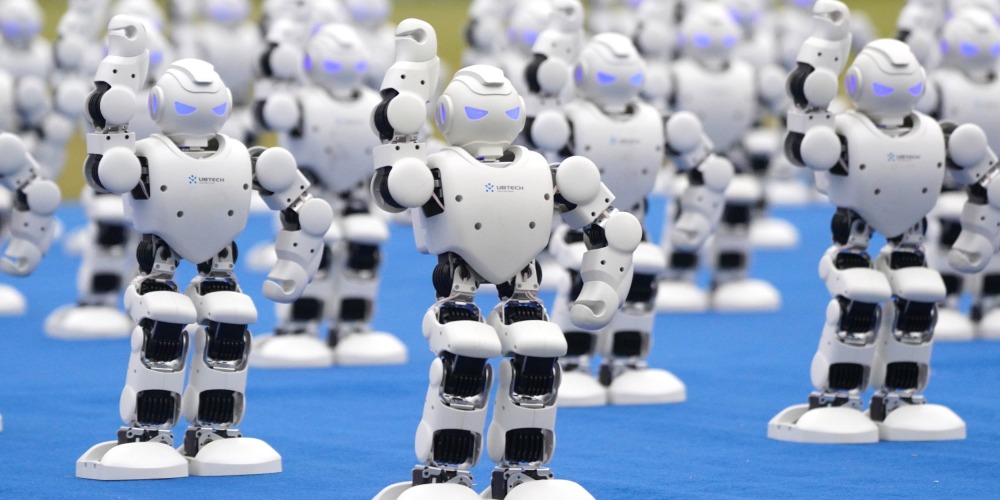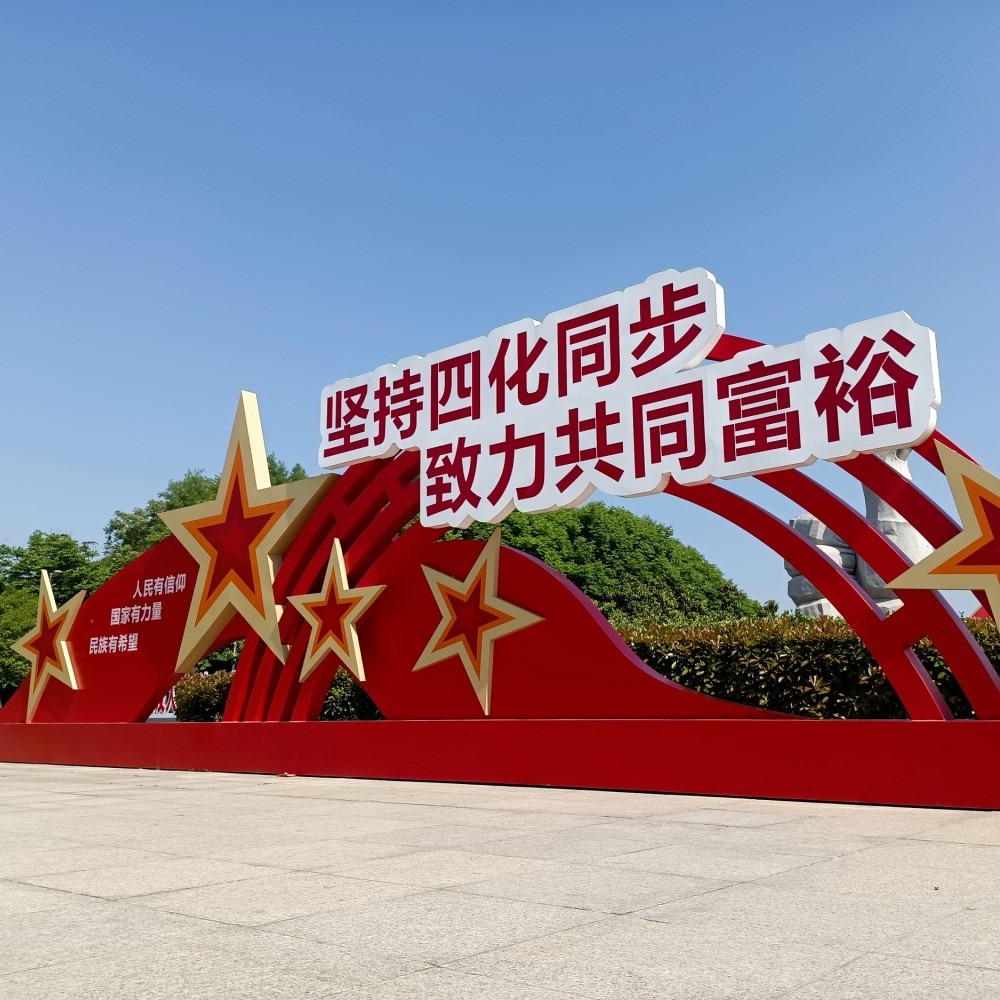刊登日期 : 2021-02-19
我原来是香港人:中国的香港人。 愿意回香港工作和生活并不奇怪。
创校(香港科技大学)初期,来港建立院系的资深同事们,大部分生长在台湾。他们早年去美国留学,继而在美国定居,成了家,养了孩子,建立了事业和地位。五十左右的年纪,置身学术专业高峰,踏上了人生的收获期,入息优裕稳定、生活丰富多彩。
正当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知识分子各找门路赶着向外跑的时候,这伙大教授们好好的日子不过,拔起根来、拖男带女跑来一个陌生地方,为的是啥?
要回答这个问题,不由得不先从自己说起。 虽然我没有生长在台湾,但是我的家庭背景和基础教育,与这些资深同事们有不少相像之处。 或许各位能够从我的个人经历里捉摸到他们的心情。
这一说,也许会说很久。 请原谅我细述30多年的心路历程。
遇抗战内战 辗转多地扎根香港
我生在砲声隆隆的上海。 父亲是清华大学保送留美的毕业生,学的是铁路管理和会计。 留学5年后回国,就职于当年国民政府的“铁道部”。早期出国的留学生不多,别人都升得挺快;他不懂得做官,干了好几年,还是个低层干部。 抗日战争打响,我军势弱,节节败退。 眼看同事们飞的飞了,走的走了;留到最后一刻,烧毁机密文件,好像总是他的任务。 从南京逃出来,几乎没赶上最后一班火车。

就在这种情况下,我在出生3个月后,被从南京逃出来的父亲,和从上海随着逃难的母亲,带到了香港。
4年后,香港终于沦陷。 父亲级别太低,轮不到跟国民政府撤退去重庆。 当然,任何一个有良知血性的人都不会替伪政府工作。于是父亲失业。千辛万苦,辗转半载,把一家老小带回上海;进入私人银行,从此依靠留学年代学到的会计本事,养家糊口。
外祸方休,内战又起。 经济全面崩溃前夕,国民政府逼使人民把一切非纸币的积蓄兑换成贬值速度以小时计的“金圆券”。 听话的爸爸,毕生积蓄化成灰烬,一家生活又没了着落。 于是,刚在上海念完小学的我,跟着父母赶去台北投靠亲戚。
台湾很乱,亲戚自顾不暇,父亲又找不到工作。不足一年,再次回香港谋生;我就在香港念了中学。
摘自吴家玮《同创香港科技大学—初创时期的故事和人物志》